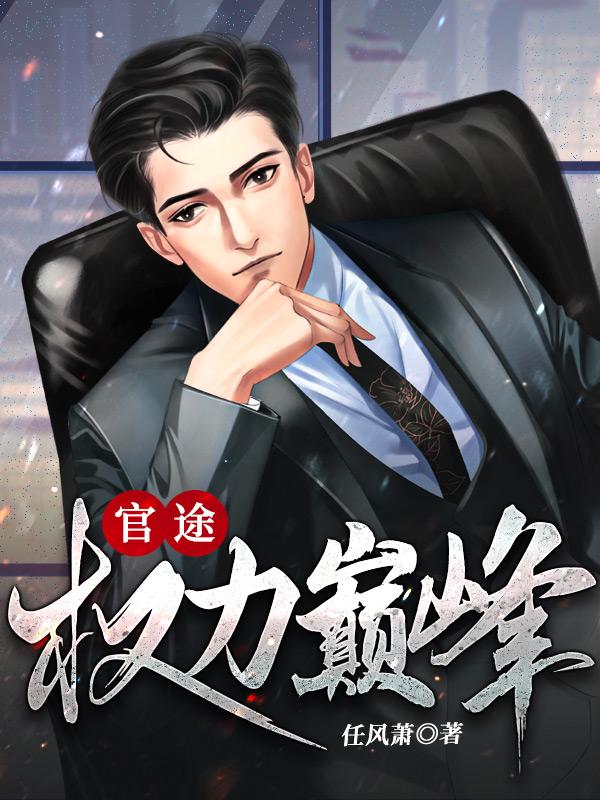书文小说>靠美食在古代爆红了 > 有劳你了(第1页)
有劳你了(第1页)
温禧将餐车推到铺子里,对两人喊道:“快来歇歇,喝点绿豆豆浆解暑。”
孙苗苗跟禔姐儿热得不行,放下手里的扫帚端起竹筒杯就“咕嘟咕嘟”地喝起来。
因着要重新装修,所以两人只把正屋和灶房先打扫了一遍,其他的等装修妥当再拾掇。温禧看着虽然陈旧但干净整洁的灶房,对二人夸道:“两位小娘子干活儿可真利索,你俩歇歇,我把东西放进灶房,苗阿姊晌午就在这儿吃,不许走!”
孙苗苗比之前开朗多了,闻言微微笑道:“那是自然,不用你说我都是要赖一顿饭的。”
一番对话惹得几个都笑起来。
中午温禧将剩的面剂子烙成炊饼,里面夹上肉排,刷沙拉酱,夹上生菜,制成中式汉堡,又炒了青菜来吃。四个人吃的肚皮滚圆,倚在前铺的破藤椅上歇息,铺子面朝着小辽河洞开,风过拂面,暑热渐消。
歇了午晌,几个人往军属所走,孙苗苗回家,温禧她们则是将剩下的东西再搬回来。刚到军属所,王氏就拿着一封信过来:“禧姐儿,有你的信,从汴京寄来的。”
温禧道谢,从汴京寄来的想必是杨芷秀的回信,接过一看果然不错。杨芷秀在信上说,王裕已然在幽州谈妥了生意,日后他们仍会运粮北上,到时候便会有见面的时机;又说若是遇到什么难处一定要去信给她或者去找她落脚都可,不要见外;芸姐儿十分想念禔姐儿和温禧做的吃食等等。
看完后,温禧心里只觉暖腾腾的,她将信塞进招文袋,打算等房子收拾妥当、铺面开业后再回信,也好让杨芷秀放心。这是第一个对她们姊妹散发善意的人,这份情谊温禧会一直记在心里。
等东西都搬空了,温禧跟王氏道别:“婶子,多谢这些日子的关照,我家不远,就在雨花巷尾,有什么事就去找我,想吃好吃的了也去找我。”
王氏由衷感慨:“禧姐儿是个有成算会经营的,你且看着,这福气还在后头呐!”
温禧掺着王氏的胳膊,直笑道:“多谢婶子吉言,那禧姐儿可就日日等着了。”
禔姐儿跟小禾也约定了要经常见面找对方玩,两个小姊妹恋恋不舍地相互话别。
回去的路上,温禧看禔姐儿兴致不高,笑道:“禔姐儿的嘴上能挂住油壶了,别难过了,等装修好了,禔姐儿就有自己的屋子了,到时候邀请禾姐儿来做客、留宿都行。”
禔姐儿闻言又兴奋起来。
下午,温禧便揣着银子去了杏前巷吴记木作铺。大晟新盖或者翻修房子,都是以木匠为尊,木匠不仅是施工者,更是设计师和监工,而泥匠和瓦匠仅负责施工。吴老汉用料扎实,又不会偷奸撒滑,温禧对他印象极好,因此今儿个温禧就要用吴师傅这一根针,串起装修队的整条线。
不同上次一般大门紧闭,今日的吴记木作铺大门洞开,里面有“哐哐”“咚咚”“嚓嚓”的做活的声音,比上次忙了不少。
温禧一进门就被二牛笑着迎住了:“温娘子来了!快坐快坐,我去给温娘子倒茶!”
温禧颇有些受宠若惊,吴老汉从后面的“木头山”里抬起头来嘿嘿笑道:“亏了温娘子的餐车,多了不少来找俺订做木活儿的,都说是看温娘子的餐车做得巧,上面还刻画了铺子名,这才找来的,这不,赚了钱二牛都多吃了几次羊肉汤饼。”
温禧接过茶恭喜道:“吴师傅财源广进呐,这全是因为您技艺精湛,肯用好料子,今儿还有要事得麻烦吴师傅呢。”
听到温禧想要翻新房舍,要请他去,还要托他寻泥匠和瓦匠时,吴师傅却没有她预想中的高兴。
温禧正疑惑呢,旁边二牛扯扯温禧的衣角,小声道:“师父脾气倔,上次去人家修缮屋子,跟相识的葛匠人、刘匠人吵起来了,几个老头子都倔,从完工后就谁都不理谁。不过……”
二牛压低了声音道:“俺们都习惯了,师娘说他们仨从年轻时就这样,过几日便好了,师父憋不住话……”
吴老汉在那头涨红了脸:“臭小子,又在编排俺啥?”
温禧脑中默默闪过“老小孩”三个字,不过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,她看向吴老汉。
吴老汉哼一声:“和泥的、上瓦的多了,咱又不是只认识他们!”
二牛摇摇头,师父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,葛匠人跟刘匠人可是出了名的实诚人,从不以次充好、偷懒耍滑。
……
吴老汉留二牛在家,背着曲尺和墨斗跟着温禧来了雨花巷,温禧想带吴老汉先看看房子,根据温禧的构想算算大致需要多少银钱,毕竟温禧如今钱没剩多少,心里有点发虚。
这房子的前铺以前是做豆腐铺的,院子里的石磨已经搬走,留下个朽烂的石磨架。西厢房之前做了滤浆区和压榨区,还留着些豆腐盒子跟晾晒架。温禧跟吴老汉商议,让他低价回收或者拿去抵消一点工费都行。
吴老汉摇摇头:“屋里这些架子固定一番倒还能用,只是这石磨架是留不得了,只有一个用处——”
见祐哥儿跟禔姐儿好奇地看过来,吴老汉开怀大笑道:“小郎君拿去烧火罢。”